结庐之处车马喧,心境安然地自偏 ——陈业新教授访谈
原标题:结庐之处车马喧,心境安然地自偏 ——陈业新教授访谈
引言
1937年,邓拓先生在河南大学撰写完成灾害史领域的肇基之作《中国救荒史》,开启了中国灾害史研究的序幕。八十年后的2017年,为了回顾前辈学者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性贡献,由闵祥鹏教授等人组成的访谈组,邀约当前学界知名学者展望灾害史研究的未来与趋势。访谈录《黎民为先:中国灾害史研究的历程、现状与未来》即将由三联出版社结集出版。
本次推出的是上海交通大学陈业新教授的访谈节选,陈业新教授是访谈组拜访的第一位学者,多年来,陈教授躬耕于灾害史等研究领域,出版了《明至民国时期皖北地区灾害环境与社会应对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和《灾害与两汉社会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两部灾害史专著,发表相关论文数十篇,成果丰硕。在访谈中,他的观点让人备受启发。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访谈节选
问:《灾害与两汉社会研究》是您的博士论文,也是当前中国古代灾害史研究的一部重要专著,您能谈一下当时撰写这本书的研究思路以及对您以后研究的影响吗?
答:可以肯定地说,这本书是我早期或第一部个人独著,于我而言,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但是,我没把它当成我的个人代表作,只是将它视为自己学术生涯的铺路石。因为今天回首反思,觉得当时的研究还有粗糙之处。由于史料的缺乏,对上古时期进行精准性的研究还没有做深做透。特别是现在很多考古资料出现后,一些内容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另一方面,因为时间有限,有些内容未能涉及;有些内容尽管当时也进行过认真的思虑,认为与灾害的关系不是太密切,也就放弃了。不过现在看起来,由于对问题的认知和理解有所不同,其中很多问题在史料充分的前提下,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而且深化以后,你所洞见的另一个世界就像万花筒,可能看到与此前认识不一样的现象。
《灾害与两汉社会研究》最大的特点就是比较系统,譬如你之前谈到的灾异思想。我为大家梳理出了一幅两汉“经常处在上帝的谴告威胁之下”“鬼怪世界”的图景,其实这就是灾异思想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这些可以从皇帝的诏书、臣子的上对中清晰的看出。当时我在看《史记》《汉书》《后汉书》时,总觉得灾异思想很重要,但是如何去研究它?我研究的是两汉时期的灾害,灾异思想只是其中的一方面,不能因为灾异思想对两汉影响尤其深远,而仅梳理这一思想,最后我觉得还是要系统化,不仅包括灾异,还要包括“天道自然”的灾害观等,同时还要对学术史上的灾、异观进行梳理,包括灾和异的影响。诚如你所说,在灾、异问题的研究上,我的研究可视为一个发端。
《灾害与两汉社会研究》的另一贡献,就是构架起相对完整的两汉灾害与社会的研究体系,从灾害状况、灾害原因、灾害思想、灾害影响,以及灾害与两汉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灾害与社会”的主题进行了整体考察。当然这些论述离不开前人的研究成果,如灾异思想对两汉宰相制度的影响等,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通史》、祝总斌先生的《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等著作均有程度不同的阐述,我在前贤宏论的基础上,将一些问题进一步系统化和明细化。2004年出版的与博士学位论文同名的独著,就是学位论文的原型。出版时,除了对引文进一步核对外,基本上是一字未动,就是希望保持原汁原味。十多年过去了,陆陆续续地看了些材料,对一些问题又有了新的认识,所以,现在我希望能够有时间静下心来做一次认真的修订,可以在许多内容上做进一步地深入探讨。譬如最近认真看《礼记·月令》,《月令》内容异常丰赡、完整,包括天象、气象、物候,还有各种各样的节令,帝王、臣僚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如果不按时令行事会产生怎样的灾异等等。这些灾异包括天灾、地灾和人祸,古代这些记载非常完整。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中,曾对两汉灾异思想进行分类,《月令》灾异思想乃其一,但那时只是简单地列举了其学说思想的内容,没有深挖和分析,打算以后做些深入研究。此外,迄今为止,学界关于两汉赈灾的深入研究也不多,在方法和整个架构上没有突破原有的模式,大部分停留在救灾应对方面,我也打算做进一步细化研究。
2006年,我参与了业师邹逸麟先生主持的《中国近五百年来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丛书的撰稿工作,丛书于2008年出版,共5本,我负责的那本名为《明至民国时期皖北地区灾害环境与社会应对研究》。与《灾害与两汉社会研究》相比,我对《明至民国时期皖北地区灾害环境与社会应对研究》比较满意。在这本书里,我基本上把皖北地区近500年的灾害环境及其社会变迁讲得很清楚了。例如,书中我对比了皖北地区的整个社会风习,尤其是民间轻文、尚武之风的演变。我通过明清时期文、武举士数量的变化及其对比,辅之以其他文献,发现从明代嘉靖年间开始,该地区社会就出现尚武、轻文之风气,文举数量少、层次低,武举数量大、层次也同样低,说明该地区民众总体文化素质偏低。这是因为什么呢?这与该地区南宋以后黄河长期夺淮入海所致的淮河中下游地区灾害环境有关。
我的家乡位于霍邱县南、六安西,属于淮河流域中部地区。在淮河中游地区,民间曾广泛流传着这样一个民谚:“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不过,该民谣描述的是北宋及其以前淮河流域的情况。唐宋时期,淮河两岸民间富足,北宋把都城定在开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当时运河开通后,江淮地区的粮食物资可以运到这里。当时的皖北,一是生态好,二是物产丰富,三是民风纯朴。北宋时,欧阳修曾任颍州(今安徽阜阳)太守,后虽多次转任他职,但晚年依然回归颍州,并度过其余生。欧阳修是江西永丰人,晚年之所以欲以颍州为家,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爱其民淳讼简而物产美,土厚水甘而风气和”。也就是说,北宋年间,皖北一带土肥水美,物产丰富,民风淳朴,与今天人们熟知的皖北可谓大相径庭。前后大有不同的原因,就是众所周知的黄河南泛。南宋建炎二年(1128),宋王朝为阻遏金兵南下,人为决河,河水“自泗入淮”。自此以后,黄河或决或塞,迁徙无定,并全面夺淮入海。在外力的胁迫下,淮河流域环境系统结构与功能受到极大干扰,生态趋于脆弱,灾害叠发。清咸丰五年(1855),黄河北去,但其所贻之患并未消失,水、旱、蝗灾依旧踵继而至。面对难以克服的环境挑战,不少地方民间走向尚武。如今皖北不少地方,每到夏日,很多小孩光着膀子在习武。这种风习在明代嘉靖年间就出现了。在上面提到的明清文、武举士的数量统计时,我把皖北的情况和皖南地区的现象做了个比较,结果显示,两个地区的情况完全相反。除了数量对比以外,我又对大量文献进行梳理、对比,发现文献中的描述性记载跟量化比较结果基本吻合。文献中描述的文风不盛、武风颇炽,也是从嘉靖年代开始的。生态环境变迁的社会影响,在这里得到了完全的体现。这些地区明清时期也经常出现农民起义。其实,捻军在皖北、豫东、鲁西南乃至整个淮河地区,存在的时间很长,可以再往上说,在晚明的时候,就有了这些风气。比如圩子,江南地区的圩是圩田,皖北地区的圩子则是寨堡。寨堡是为了维持社会治安,我个人认为其实同于东汉时候的坞壁。由于社会动乱,家境富裕的家庭,以自然的圩子即水塘为屏障,筑寨自保。圩寨的修筑,也与自然灾害有关。由于灾荒年年,民间尚武好斗,一些因灾积年致贫的民人,白天从事农业生产,晚上则几人结伙,到外面行梁。行梁就是打劫。这一带没有大的土匪或匪帮,而以成群结队的小偷小盗为主。这种情形,即使在建国后,我们老家那里也出现过。我记得非常清晰,小时候经常听到某人家境稍殷,过年前宰杀了生猪。为安全起见,一般都会把猪肉吊挂在草房的梁上。但晚上稍不留心,别人就可能把你的门窗从外面锁上,然后搬个木梯,从你家草房顶上把草扒开,然后把挂在梁上的猪肉提走。我认为,这就是明代以来灾荒环境下形成的民间行梁之风。强者抢夺而生,那么弱者如何而存?泥门趁荒,是皖北明清时期突出的社会现象。一般而言,秋季作物收获完毕后,民人即离家四散趁食。灾荒不断,家中可能徒有四壁。外出时也不锁门,用泥把门糊起来,挎着个篮子、拿个竹棒,到外面去讨饭。一开始是为了基本的生存,日积月累,慢慢就成了一种习惯,并形成思维定式:冬天在家里什么也不能干,窝在家中白白吃粮食,而在外面走着,最起码一天的几顿饭解决了。到第二年春天农忙时,外出者鱼贯而回。所以,这时的外出行乞,是为了备荒。民国时期的皖北,是全国闻名的流民输出地;今天的皖北,是远近皆知的农民工输出地。农民外出务工,在今天看来是时代的产物,但在皖北,其规模之大,不惟现实的动因,历史文化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因此,我个人认为,我们今天的社会治理,千万不可忽略其历史之源,现实与历史总有割舍不断的联系。
问:从邓拓先生《中国救荒史》出版到现在,灾害史研究面临着很多的问题,比如研究的程式化、套路化,缺乏量化与实证,您觉得灾害史研究应该如何摆脱这种困境?
答:对于灾害史研究动态,我本人始终高度关注,尤其是学位论文。为什么这么关注学位论文,因为这些论文的作者都是年轻人,是未来灾害史学术研究的担当者,决定着将来中国灾害史的研究水平。看这些论文,主要想看一下他们在视角、内容、观点、史料、方法上是否有突破。但很遗憾,不少论文水平颇为低下,有的连最基本的学术训练都缺乏。譬如史料方面,有些论文一看就是没有查阅原始史料,直接引用二手材料,别人错什么,他就错什么。另外,现在许多文献可以电子检索,这个检索非常方便,省去了以往研究搜求文献之苦。但是,电子检索完以后,一定要核对原文。事实上,很多年轻人忽略了这一环节,以致引文漏缺字、错字、句读不当等问题异常突出,更不用说对史料进行深度挖掘了。
你刚刚说的灾害史研究存在的那些问题,我觉得可以通过学界的共同努力来解决。首先是资料的深度挖掘,这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面上的广度,另一个是点上的深度,就是对史料的深入分析。比如说我们在研究灾害问题时,往往拿到一两条史料就下论断。目前,学术界对历史灾害资料基本上没有进行全面的整理,研究者多各自为政,不仅重复劳作,而且效率低下,质量也得不到可靠的保证。没有文献保障的基础,遑论深度挖掘资料,那么,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自然是奢望。
其次是方法的创新。目前所见绝大多数灾害史研究成果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流于文字描述。“文献分析法”是历史学看家的研究方法,但一些成果只见“文献”,而难觅“分析”。“分析”包括定性、定量两个方面。缺乏定量、定性的分析,难以获得学界的认可,所以灾害史研究往往变成了研究者的“自娱自乐”。迄今已成功举行了十三届的“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年度学术研讨会,较早时期的参会者多来自如地震、地理、气候、水利、地质等自然科学界,但历史学研究者进入灾害史研究并积极参加会议后,自然科学的学者认为历史学者的研究缺乏科学的方法,而历史学界则以其研究存在“非人文化”的倾向,灾害史研究陷入“两种文化”的窘境,彼此难以形成良性对话的局面,存在历史学的灾害史研究成果如何为自然科学界认同的问题。在前不久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夏明方教授组织的“中国灾害史料整理与数据挖掘”学术研讨会上,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的方修琦教授再此提到这个问题:你们认为我们的研究缺乏史料的支撑,我们觉得你们的研究不能解决问题;你们讲的史料我们也知道,我们觉得你们定量研究做得不够。但是,我觉得有些问题做定量研究也是不太现实的,比如说古代灾害史研究,你做隋唐,我做秦汉,如果想把它定量的话,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史料不够丰富,而且文献记载本身也不详细。这种情况下,越是精准定量越容易出问题。因为定量的基础是文献,文献本身有问题,所以这种定量出的结果跟实际情况必然有差异。那么,哪些时间段可以做定量研究呢?明清及其以后的时期,基本具备了定量研究的条件。明清时期,每个县地方志书中的灾害记载具有很强的连续性,完全可以做定量分析。但是很遗憾,因为资料面比较广,量比较大,量化研究比较麻烦,所以在明清灾害研究方面,有关成果基本上没有定量分析,代之的则是简单的年次统计。
刚才咱们讲的也可算是灾害史研究落入模式窠臼的表现吧。灾害史研究究竟包括哪些内容?我想,作为最基本的研究框架,一是灾害的内史研究,即灾害的基本情状,包括灾害次数、灾害等级参数化处理、灾害的频率、灾害的空间分布、灾害原因,这是从整体是角度而言的。另外还有灾害个案或专题研究,譬如场次灾害、特大灾害研究等等;二是灾害外史研究,也就是灾害与社会的研究。历史学主要是研究人类社会的,而灾害则主要是就其对人类的影响而言的,因此灾害与社会永远是历史学关于灾害研究的核心或主要内容。这方面的内容非常广泛,但凡政治、经济、文化,无所不涉。政治方面包括政治制度、职官任免、法律制度等,经济方面则有赈济(国家、地方官府和社会等)、国家财政与社会经济状况等,文化方面则如荒政思想、民间信仰、史书书写、灾荒文献等。灾害的直接后果就是对社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严重者可引发社会动乱,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很多都与灾荒的诱因相关。由灾害产生的相关文化,在传统社会里也十分常见,如民间普遍存在的祈雨、祈晴活动及其仪式,以及龙王信仰、城隍信仰和龙王庙、城隍庙景观文化等。而且,在不同地区,同一信仰还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而使得文化呈现出差异性、丰富性的特征。目前所见灾害史研究成果,上述有关方面都曾有所触及,但大多数是泛泛而谈,缺乏深入的研究。因此,突破窠臼,无外乎要在两方面多加努力:一是要在占有丰富史料的基础上,从不同视角、不同方面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剖析,深化研究,发现存诸史料和传统社会中但罕为人们关注的历史沉积,揭示历史的本质与规律。二是积极拓展研究空间。灾害史的研究内容非常全面,早在1920年代,美国传教士马罗立(W. H. Mallory)就称传统中国是“饥荒的国度”,也就是说传统中国留有浓郁的灾荒烙印,她的一切,如生态、农业、人口、农村社会、制度与体制、社会秩序、文化与思想等等,都可以从灾荒那里找到答案,或能够以灾荒对之加以合理的解释。这样来看有关研究,我们说,灾害史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拓展。
最后,我还要多讲一句,就是治学态度的问题。现代社会绚烂多姿,充满诱惑,机会无处不在,尤其是在上海、广州等商业气息特浓的大城市,追求时尚的年轻人难免不受其影响而心旌摇曳。而且,姑且不和工程技术类学者相比,就是和社会科学研究者相比,同样是从事学术研究,彼此的回报也是差悬很大。这种情况下,作为青年学者,首先就要调整心态,既然选择了史学,就要做好坐冷板凳的思想准备,理性面对喧闹的世界、富足的他者,潜下心来做自己可以做的事,否则于事无补,于己不利。驿动的心境、躁动的心态,永远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更不可能拿出优秀的成果。
陈业新教授简介
 陈业新
陈业新
1967年生,历史学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1996年、2001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所,分别获历史学硕士、博士学位(历史文献学专业)。2001年9月-2003年6月,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2003年6月至今,工作于上海交通大学,从事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出版独著3部、合著多部,发表论文60余篇。
研究方向:秦汉灾害史、社会环境史、灾害文化与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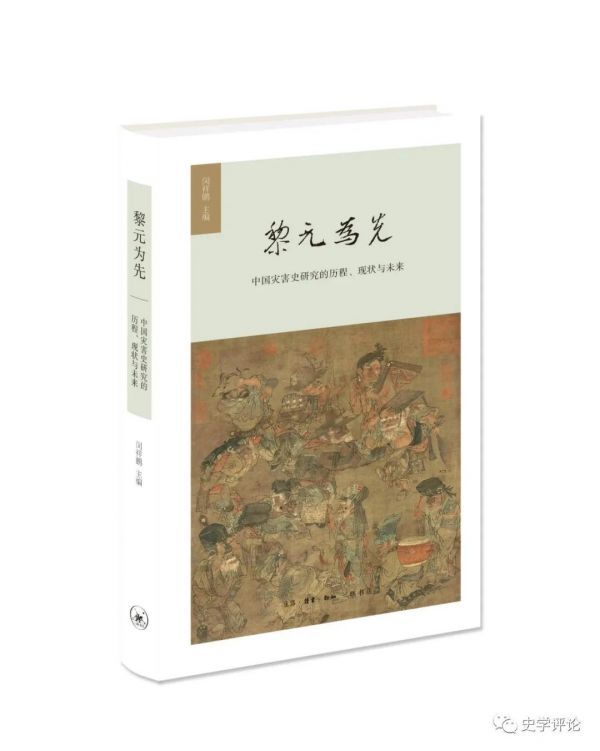 节选自《黎元为先:中国灾害史研究的历程、现状与未来》,三联出版社,2020年。
节选自《黎元为先:中国灾害史研究的历程、现状与未来》,三联出版社,2020年。
责任编辑:
相关知识
结庐之处车马喧,心境安然地自偏 ——陈业新教授访谈
《饮酒》(其五)情景默写专练(含答案)
悦读丨平安是福,平淡是真,平静是乐
云霞绕地偏
安然论币:4.2比特币维持区间震荡,区间是否打开还需确认
党员干部的“田园”守则
陶渊明:饮酒一生,独得悠然之趣
党员干部要化繁为简
名人堂·访谈|哲学家陈嘉映:我们要培养一种新的“心智技能”,把注意力收拢在身边
联合深业竞投“未来之门” 万科81亿拿地创年内投资纪录
网址: 结庐之处车马喧,心境安然地自偏 ——陈业新教授访谈 http://www.shhpp.com/newsview5025.html
推荐社会
- 1王灿前夫 王灿的第一任老公 8297
- 2包养百位嫩妹一夜9女,台湾富 6776
- 3猎艳?猎物!男子出国猎艳被间 4565
- 4这个打架子鼓的王安宇也太帅了 4405
- 5神仙选手!16岁全红婵已跳出 4028
- 6圆桌|从人和故事出发,谈谈推 3870
- 7读刘慈欣的《三体》:技术统治 3804
- 8真希望他们只是万千寻常人家中 3613
- 9导播:人都到齐了,来个大杂烩 3435
- 10孟子义李昀锐《奔跑吧》路透曝 31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