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外部”:柄谷行人的思想历程
柄谷行人作为日本战后具备世界影响力的思想家,自20世纪60年代在日本文坛崭露头角以来,其写作始终就拒绝安于一隅,不断游牧于各门知识疆域。他以横跨文学、哲学、社会理论、政治经济学的批评方式,持续挑战既有的知识体系。

柄谷行人(1941— ),日本兵库县人。享誉国际的日本当代哲学家、思想家、文学批评家。
不过,这种多重的理论面向,既让人着迷,也时常令人困惑: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他这些发散的学问,他的思考是否有更深层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轨迹?
《迈向“外部”》这一汉语学界首部系统介绍柄谷行人的专著,以“外部”作为核心概念,将柄谷的思想发展梳理为四个阶段——从早期对文学形式的批评,到中期对日本文学传统话语空间的突破,紧接着是往“后现代思想”的转向,再到晚近以全球视野构建宏观理论与制度批判。作者不仅细读了柄谷的主要文本,更将其思想整体性地置于战后日本社会的历史语境中予以考察。因此我们也能看到,柄谷从不满足于理论层面的革新,而是坚持让自己的思想迈向“外部”,刺入活生生的社会变革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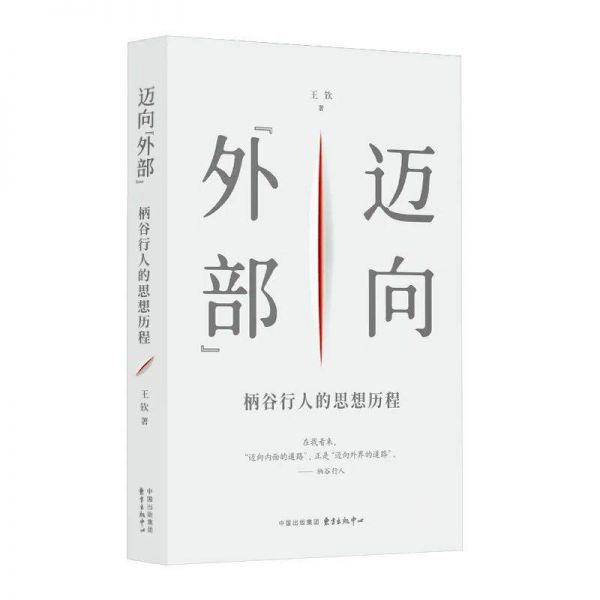
《迈向“外部”:柄谷行人的思想历程》
王钦 著
定价:75.00元
东方出版中心·象形文字
2025年7月
★首部中文系统研究:
首次全面梳理柄谷行人思想演变脉络,填补中文世界研究空白。
★ 跨学科思想全景:
深入解析其横跨文学、哲学、社会理论的核心观点,揭示如何打破知识封闭,走向“外部”。
★ 直面时代与现实:
置于战后日本社会背景,展现思想如何回应现实困境,激发我们对当下的重新思考。
作者简介
王钦,美国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博士毕业,现为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东亚文化、西方后现代思想等,专著有《“零度”日本》,并译有柄谷行人的《探究(一)》《探究(二)》等。
目录
引言
作为批评家的柄谷行人
第一章 “意识”的终点与“自然”的起点
——《意识与自然》与柄谷行人早期批评的问题
第二章“意义”的悲剧与“悲剧”的意义
——《论麦克白》与方法
第三章“内面”与“制度
——重访《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
第四章 迈向“货币形而上学”的“外部”
——以《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为中心
第五章从“外部”出发
——论《探究(一)》
第六章专名·他者·交换
——论《探究(二)》
第七章“交换样式”的变形与“力”的形成
——柄谷行人的后期思想
参考书目
柄谷行人简略年谱
后 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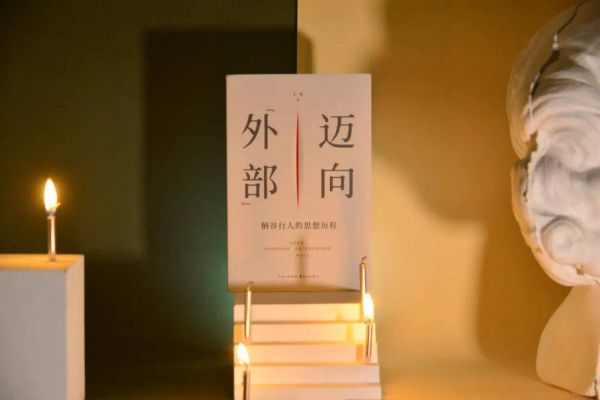
作为批评家的柄谷行人
引言
在当代日本思想史上,柄谷行人(Kojin Karatani)无疑是一位不可忽视的思想家:自20世纪60年代末凭一篇探讨夏目漱石的论文获得“群像新人奖”以来,柄谷在其每个思想阶段留下的大量著述,都引起日本学界的关注和讨论。而以70年代撰写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为标志,柄谷的著作逐渐在海外学界产生影响力,并陆续被翻译为英文、中文、韩文、德文等,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大量读者。在过去数十年中,日本国内有关柄谷的思想的集中讨论和整理,曾经数次见于《现代思想》《文学界》《国文学解释与教材的研究》等著名的思想杂志上;至于日本之外的地区,则不仅在美国、中国、韩国等国的大学中,研究者们围绕柄谷的思想展开多次学术会议和研讨班,甚至些社会和群众运动乃至政治家也受其著作影响。更有论者认为,从60年代末至90年代后半叶,“柄谷行人无疑以一己之力体现了日本的批评图景的趋势”。
然而,柄谷也是一位在思想上难以定位和概括的作者:从其早期的文学批评到对于马克思的独特解读,再到亲自发起的“新联合运动”(New Associationist Movement)最后到其后期构筑的“交换样式”理论。柄谷似乎自亮相于日本批评界以来便一直在不同的领域、对象、实践方式之间进行不断地移动和试错。在论述的方法和风格上,柄谷不断穿梭于文学、经济学、哲学、美学、语言学、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数学等领域,从不满足于在具体的某个领域“安营扎寨”。在社会认知的层面,从被视为继小林秀雄、吉本隆明、江腾淳之后的新一代“批评家”代表,到被视为兴盛于80年代日本社会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即所谓“新学院派”)的领军人物之一,再到被视为“对于现代哲学、哲学史和政治思想做出根本性的原创贡献”的伟大思想家,柄谷的身份似乎从未稳定在某个特定的范畴或位置。尽管如今有越来越多的论者愿意将柄谷称为“哲学家”,但或许“批评家”仍是一个更恰当的称呼。与此同时,对于任何试图整体性地梳理柄谷的前后期思想的尝试,将柄谷视为“批评家”的做法或许是一个颇具生产力的视角或线索。至少可以说,这符合柄谷的自我定位。例如,柄谷在1990年的一次座谈会上谈及自己的早期批评时说道:
我在60年代选择批评这一领域的一个原因,或许是因为它能包罗万象。我当时并没有把批评仅仅当作文学批评来看待。换句话说,批评没有界限,它可以涉及任何领域。虽然在那个时候我的想法还很模糊,但我隐约觉得批评是一种无界限的东西,甚至能够消解界限。后来,我对此有了更明确的认识。
真正对批评有了自觉是在1975年后,那时对我来说,批评开始接近康德所说的“批判”。康德的批判是一种在没有预设标准或立场的情况下进行的自我反思与检验。在某种意义上,它可能会挑战一切立场:但它并不结束于怀疑主义,而是从没有标准的状态开始探索。对我来说,1975年以后的批评,关注的对象已不再局限于文学,而是更多转向哲学、文化科学、经济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尽管这些学科有各自的标准,但在我看来,它们其实没有固定的标准,所有这些学科归根到底都是基于语言的。
当然,我们不能从这段话得出结论,认为柄谷的思想落足于对“语言”的推敲——的确,对语言本身的关切构成柄谷在某一思想阶段的重要议题,但这种关切本身也将随着其思想的展开而逐渐改变。在我看来,上述引文中更关键的地方有二。第一,“批评”对于柄谷始终意味着在论述方法和对象上保持开放性和非规定性——不同于具体的学科领域,“批评”对于柄谷来说从一开始就是能够横跨各种领域、边界、前提、范畴的文类,甚至是一种非文类的文类或“去文类”的文类。因此,无论是对马克思和《资本论》的解读,还是对康德的解读,抑或是对柳田国男的解读,在柄谷这里都成为“批评”(有时他也称之为“文学批评”)的一种实践。(在某种意义上,如柄谷自己明确意识到的那样,他对于“批评”的这种开放式的、非限定性的理解,与20世纪60年代流行于欧美学界的“[文学]理论”颇为类似。)
第二,在上述引文中,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一点是,柄谷表明,自己对于“批评”的理解有一个逐渐自觉的过程。不过,这里的“自觉”指的不是关于方法和对象的自觉;相反,它指向的是某种根本性的生存方式。用柄谷自己的话来说,“批评”不是“理论或方法,而是一种充满矛盾的、脆弱的存在方式:既属于一个体系(话语空间),又不属于这个体系”,而这种特殊的存在方式的不稳定性足以把人“撕裂”。
毫无疑问,上述引文中提到的“1975年以后”,具体指柄谷撰写《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和《柳田国男试论》的阶段。然而,尽管柄谷说自己直到这时才“真正对批评有了自觉”,但这一表述绝不意味着此前他未曾反思过“批评”乃至“批评家”。恰恰相反,“批评家”的身份对柄谷而言始终是一个问题。不如说,康德意义上的“批判”使柄谷能以更系统的方式重新看待自己一直以来在“(文艺)批评”的名义下展开的工作。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只有恰当把握柄谷在早期作为“文艺批评家”登场阶段对自己“批评家”身份的思考,才能更好地理解柄谷在70年代对于“批评”的“自觉”
值得注意的是,柄谷在1971年发表的文章《批评家的“存在”》,直接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了一番艰难的探索。在这篇文章开头,柄谷引用了前辈批评家江腾淳在其著作《小林秀雄》开头写下的一句话:“人可以成为诗人或小说家。但是,成为批评家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小林秀雄那里,“批评”和“批评家”的含义同样得到了批判性的考察,甚至小林在昭和初期作为“批评家”亮相日本文坛不久后,便撰文《失去批评家资格》来反思自己的“批评家身份。而在柄谷这里,这个问题如今显得更复杂,因为由小林秀雄开创并由江腾淳等人继承的“批评”,在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然成为一种既定的独特文类,而柄谷自己着手的“文艺批评”也已顺理成章地被归人其中。无疑,这与柄谷对于“批评”作为“非文类的文类”的期许相去甚远。换言之,对于柄谷来说,如今问题的出发点不再是“批评何以可能”,而是这种在现实中始终已经成立的文类与自己“批评家”身份之间的张力:
在我们出生的时候,批评已经作为一种分工形态而存在了。我开始写作评论,无非也是出于这个原因,但是“成为批评家”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因为即使批评存在,[写作者]也必须要成为批评家。不存在天生的批评家。所以,在一个人成为批评家的过程中,就存在着某种不可避免的因素,使得他无法采取除此以外的其他表达(生存)形式。这种因素不可能是偶然写点评论。毋宁说,确实可能存在的情况倒是,只有批评家才能进行批评。这也就意味着,“批评家”是通过放弃某些东西而获得的一种精神的存在形态。
不同于既定文类意义上的“批评”,“批评家”并不是一个人出于自己的意愿而主动选择的某项活动或职业,更不是随性而至的结果;针对某些作家或文本撰写一点文艺批评,并不能让人因此成为“批评家”。恰恰相反,“批评家”产生于一种决定性的“放弃”:柄谷在此没有具体阐述这种放弃的内容,但从上下文可以得知,这种放弃不仅指向其他表达方式或类型——如小说、戏剧或诗歌——甚至指向“语言表达”这一根本前提。也就是说,这里的放弃与是否从事虚构写作无关,而是意味着“批评家”不可能站在一种客观、中性或超越性的立场,针对某个文本做出批评;毋宁说,正是意识到任何“批评”都指向表达的不可能性,指向写作者自身立场和前提的危险和脆弱,甚至最终指向“批评”的不可能性,才使得一位写作者能够在不可能的写作中成为“批评家”。归根结底,“批评家”意味着写作者对于“失去批评家资格”的必然性的自觉,对于这一点,柄谷写道:
在批评这里,比起写什么,问题是怎么写。例如,无论愤怒和悲哀是多么真率,一旦用语言表达出来,就变得平庸而无法感动他人,这是因为语言一举跨越了原本难以传达的失语的沟壑而诉诸社会化了的陈词滥调。尽管是确实存在的愤怒和悲哀,将它们变成语言的时候,我们就只能获得他人的愤怒和悲哀。无论书写的意图和动机是什么,我们都必须通过与社会性语言的搏斗才能实现真实性。所以,“怎么写”不是技术性问题,而是最具伦理性的问题,一切都包含在此。只有在这一地点,批评才能变成文学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批评才确实触及批评家自身的存在。
在这里,“写什么”和“怎么写”这一在各国现代文学史上不断被讨论的经典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不如说是“语言表达”本身的限度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谓的“真实性”和所有现实主义表现手法都无关,甚至与现代主义所强调的“语言的物质性”也无关。既然语言本身注定是社会性的(不存在“私人语言”),那么,作为“与社会性语言的搏斗”的一种不可能的写作,“批评”就必须利用语言来和语言表达的前提本身、语言的可能性条件对峙。当然,如果将这里的论述翻译为情感的独特性和语言再现的普遍性之间的矛盾,那么柄谷的思考并没有提供太多新的内容;然而,柄谷试图传达的“批评家”的(不)可能性的条件毋宁说是,“批评家”必须始终站在两种彼此不可调和的事实性之间:方面,语言只能通过“陈词滥调”的方式、通过“他人的愤怒和悲哀”的中介,以不充分的、错位的、失焦的方式表达固有的、本真的、独特的东西,以至于“失语的沟壑”根本而言无法被克服;另一方面,我们通过语言表达自身的情感并实现与他人的交流,甚至对虚构人物的喜怒哀乐感同身受”,同样是一个始终已经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得到实现的事实。毫无疑问,当“批评家”站在上述两种事实性之间的时候,他并不能占据任何实质性的位置或立场甚至这里的事态无关乎做出选择或决断。毋宁说,这种“之间”的不稳定性、游移性、非实质性,对柄谷而言恰恰是“批评”的意义所在。
本文为“引言:作为批评家的柄谷行人”节选
象形文字是东方出版中心旗下的图书品牌,自2021年以来,致力于发掘经典思想作品与反映海外学术动态的新作,打造面向社科人文读者群体的学术精品。目前,本品牌已出版柏拉图、波埃修斯、马基雅维利、黑格尔、尼采、法农、施米特、布鲁门贝格、米歇尔·亨利等经典作家的代表作,并引进了阿兰·巴迪欧、韩炳哲、达里安·里德等前沿思想家的作品。
相关知识
迈向“外部”:柄谷行人的思想历程
王钦评柄谷行人《探究(二)》|专名与他者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柄谷行人《历史与反复》
刘柄序:锋芒毕露的少年狂想
李菲授她以柄爱情
走进阳明先生的精神世界 领略传统文化魅力 南昌红谷滩大剧场上演话剧《阳明三夜》
李柄熹说为张雨绮吃醋,却被对方伸手阻止,不像恋人更像经纪人
汪小菲李柄熹同场亮相 张雨绮新欢旧爱同台引热议
西垂古镇天水杨家寺,王柄先生,一位才华与成就交相辉映的学人
陌上行人似玉,公子举世无双
网址: 迈向“外部”:柄谷行人的思想历程 http://www.shhpp.com/newsview334928.html
推荐社会
- 1王灿前夫 王灿的第一任老公 8186
- 2包养百位嫩妹一夜9女,台湾富 6766
- 3猎艳?猎物!男子出国猎艳被间 4559
- 4这个打架子鼓的王安宇也太帅了 4405
- 5神仙选手!16岁全红婵已跳出 4026
- 6圆桌|从人和故事出发,谈谈推 3802
- 7真希望他们只是万千寻常人家中 3609
- 8读刘慈欣的《三体》:技术统治 3514
- 9导播:人都到齐了,来个大杂烩 3435
- 10孟子义李昀锐《奔跑吧》路透曝 3174










